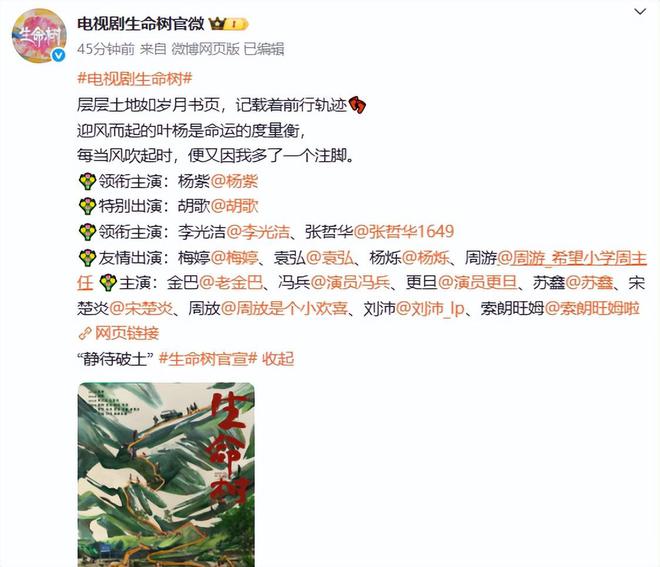《性别打结:拆解父权制遗产》,[美]艾伦·约翰逊著,杨晓琼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9月出版,579页,88.00元
关于父权制,电影《奥本海默》里有一段颇具象征意味的情节。已经开始执行“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想要离开研究基地,与情人琼·塔特洛克见面。考虑到计划的“绝密性”,他必须得到军方的安全批准。后者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代价是奥本海默必须配合保密要求,即不能与任何“可疑人士”——包括他信任的朋友——联络。当奥本海默终于见到了琼,琼对奥本海默说,“你在我的生活里来来去去,却不必告诉我为什么,这就是权力”。然而等到战后所谓“奥本海默事件”爆发,奥本海默在一场非正式听证会上“受审”,这一事件——权力的赋予——却成了攻击甚至是羞辱他的武器。最后面对妻子“你为什么不反抗”的诘问,奥本海默沉默不语。
或许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很难成为奥本海默:拥有绝世的头脑,“奉命于危难之间”——在极端的“例外状态”下被赋予特权,然后随着状态解除、特权丧失被推入谷底。然而令如此命运发生的父权制,实际上至今仍在以相对弱化、日常化的形式困扰着所有人。

电影《奥本海默》海报
“何谓父权制?”在《性别打结》的开头,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给出了他的定义:“一个遵奉父权的社会,通过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和男性中心来促进男性特权。”(第8页)不难想到维系这样一种制度的关键,在于对“第二性”——女性的压迫。然而它还有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关键面向,即“它也是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组织起来的”(同上)。作为一名在父权制社会持有主流身份(白人、男性、异性恋)的学者,约翰逊这一研究最大的贡献,便是理清了父权制与他这样并不受其压迫,但受其控制的男性个体之间的关系:父权制“是它,不是他、他们或我们”(第二章标题)——当一个男性拒绝反抗甚至仅仅是去理解父权制,他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身份与一种控制他的模式等同起来,进而使得自己的存在与之高度绑定,反抗它即是反对自身,而他所遭遇的挫败一定与它无关。然而事实恰恰是一切男性气概带来的灾难皆源于父权制对于男性特权的赋予:想想《白鲸》——在很大程度上,这部名著可以视作对父权制美国“国家神话”命运的预言——中的亚哈船长,倘若他没有将“复仇”想象成自己必须执行的“男性使命”,又怎会执意追逐那“恐怖而不可测”的白鲸,最终招致全船随自己一道覆灭的结局。
经由约翰逊的这一辨析,男性参与到反对父权制乃至女性主义事业的真正理由显然易见。他有必要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她”者居高临下的同情——倘若如此,那他依然沉浸在父权制所期许的“怜香惜玉”当中;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解放他自己。我们甚至还能回答那个聪明如奥本海默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无法反抗,仅仅是因为“如果你无法想象没有这个游戏的生活,那么除了做符合期待的事情,你是看不到太多其他选择的”(62页)。奥本海默式英雄的一切功绩皆由这一游戏取得:父权制下的男性被鼓励风流倜傥、张扬个性、实现抱负,然而一旦触动了这一体制的控制警报,这些特权便会转化为不检点、不可理喻、不切实际的攻击——恰如它一开始便对女性发动的“预防性审判”,而它正是通过这样的审判将权力从女性身上夺走,然后支出可控的一部分收买男性,并随时准备将其收回。不难看出,在这个游戏中,真正丧失的是“我们”的权力——没有人能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前提下成为他/她自己——这便是我们受困于“性别之结”的理由,也是拆解父权制遗产、想象另一种可能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会这样——父权制作为“最小阻力路径”
与其他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著作相比,《性别打结》最大的特色,在于全书以大量篇幅铺设关于理解性别议题极富实践性的社会学进路,而这自然与约翰逊作为一位社会学家长期思考的问题相关:“这个世界充满了如此多不必要的痛苦……以至于除非我们刻意否认或视而不见,否则我们就一定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借助工具来了解问题的走向,并设想如何改变现状。”([美]艾伦·约翰逊,《见树又见林》,喻东、金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