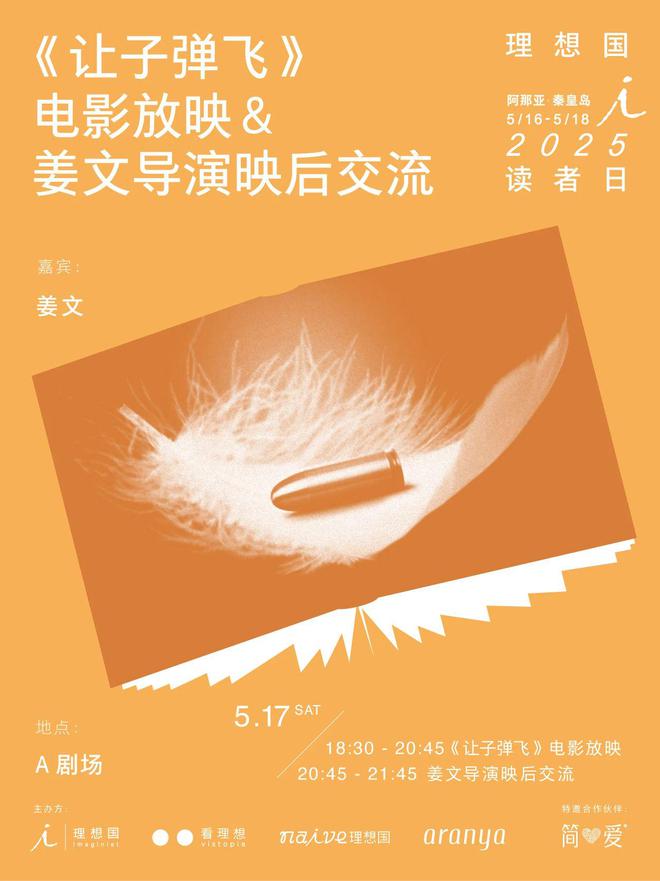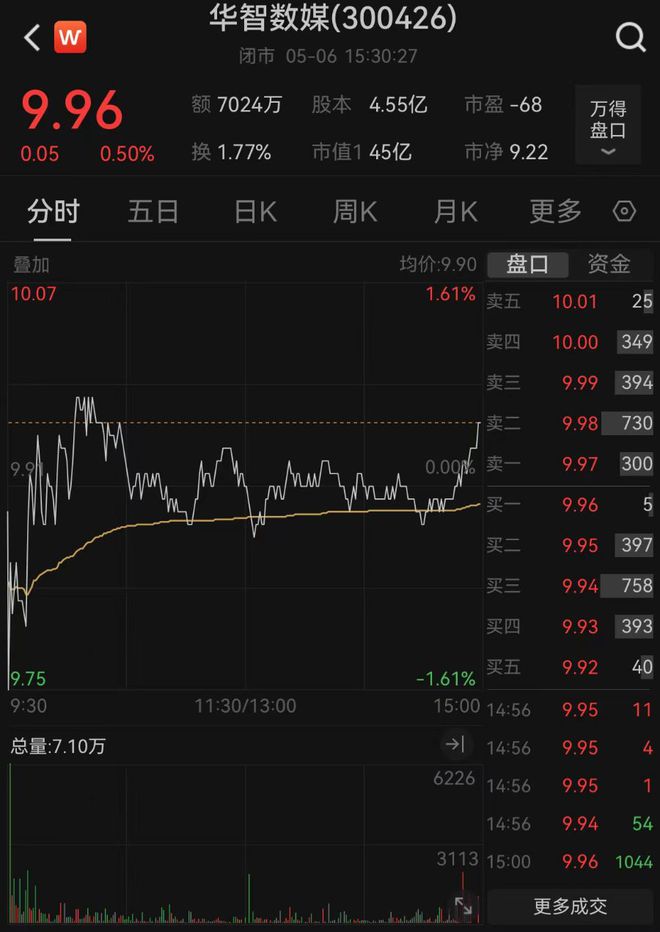克里莫夫和他的摄影师阿列克谢·罗迪奥诺夫之所以使用斯坦尼康,并不是为了在视觉上获得令人着迷的平滑效果,而是着力展现这场纳粹对白俄罗斯人施行的种族屠杀中,种种人物的行动轨迹。这部电影的视觉方案十分「主观」——以弗廖尔视角来呈现——但实际上它是通过弗廖尔和其他角色的视角,轮番展现的。通常,弗廖尔看不到伤害他的究竟是什么。
除了这些高超的技巧,克里莫夫在艺术上戏剧性的生命力还在于他对变调的控制,以及他对惊喜的驾驭——这些都是成就《自己去看》这部杰作的原因。尽管这部电影很骇人,但我们总是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部分原因是我们希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能解释之前发生的事情。

克里莫夫童年时期对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从城市中撤离的记忆为这部大胆的电影提供了灵感。另一名编剧安列斯·阿达莫维奇直接利用了他1942年和1943年在苏联白俄罗斯游击队的青少年经历。阿达莫维奇已经凭借他基于史实改编的小说《哈廷故事》,在文化界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本1972年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叫弗廖尔,小说的内容则描写了一场村庄大屠杀和大火。1975年,他凭借讲述纳粹屠杀白俄罗斯村民的史诗般的作品《走出困境》(与扬卡·布莱尔和弗拉基米尔·科莱斯尼克合著),成为了纪实性新闻写作的先驱者。
阿达莫维奇这种将口述历史和编年史融合在一起的写作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在1985年出版了《我还是想你,妈妈》,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基于苏联卫国战争中幸存儿童的描述。(它去年才出版了英文译本。)当时克里莫夫和阿达莫维奇筹备制作《自己去看》时,克里莫夫的妻子,才华横溢的拉莉萨·舍皮琴科正在准备自己那部令人瞠目结舌的二战影片——根据白俄罗斯作家瓦斯里·贝科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上升》(1976)。
《自己去看》从一种荒诞闹剧的氛围中开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怪诞的噩梦,最终以劫难收尾。在影片开头,村里的一名老者警告两个男孩不要从埋葬游击队的沙子里挖武器。(我们最终明白他担心党卫军在暗处观察这些年轻聪明的家伙。)一个有淡黄头发的男孩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的穿着,看上去像是要去北非参加坦克战,模仿着这名老者,就像自己是纳粹教官一样。当这个不守规矩的男孩面对镜头走来时,我们才意识到,他正在和躲在灌木丛中的弗廖尔说话。当他们俩向远处跑去,冲向装满苏联步枪的战壕时,字幕出现。弗廖尔需要一把枪才能成为梦想中的战士。

这个开场就像贝克特或尤内斯库戏剧中的开场白一样刺耳和荒谬,只不过它更加真实。当一架德国飞机在男孩们的头顶盘旋时,他们躲了起来。飞行员真的会瞄准像这些男孩一样渺小的目标吗?(事实上,是的。)在一系列刻意而又参差不齐的镜头中,克里莫夫描绘了一些没有立竿见影的动作——比如弗廖尔脸朝下趴在战壕里,他的身体紧握着,颤抖着,竭尽全力想把沙子里的步枪拔出来。这位导演制造了某种可怕的阴谋:我们如何看待弗廖尔这一难以理解、不协调的动作?
很快,克里莫夫把我们领进了弗廖尔的家,这个男孩拿着步枪,坐在母亲身旁,对心烦意乱的她傻笑着。我们意识到,我们看到的,影片中的地区正处于彻底的、灾难性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克里莫夫将痛苦的母亲的近距离镜头与弗廖尔的白痴笑容并列在一起。她挥舞着斧头,要求弗廖尔把她和他的双胞胎姐妹也杀了——考虑到如果弗廖尔走了,她们会多么无助。在他和拿着斧头的妈妈争执之后,弗廖尔滑稽地向女孩们做了个手势,让她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在玩。

当两名游击队员,其中一人穿着被丢弃的德军装备,假装自己是在迫使弗廖尔和他们一起去,目的是误导任何纳粹间谍时,这场「游戏」就变得更加可怕了。他们擦伤了弗廖尔的脸,把他和一位说德语的无名男子一起扔进一辆手推车里,然后嘎嘎作响地进入森林深处。
克里莫夫令人不安的艺术结合了神秘和充满激情的对抗:他将我们推入行动,并且以狂热的速度展开,迫使我们与弗廖尔一起前进。这位导演加强了我们与这位笨拙的青少年的联系,因为他跌跌撞撞地穿过了一个临时的党派营地,那里纪律松散,贵宾是一头即将被屠杀的奶牛。